http://www.chufengwang.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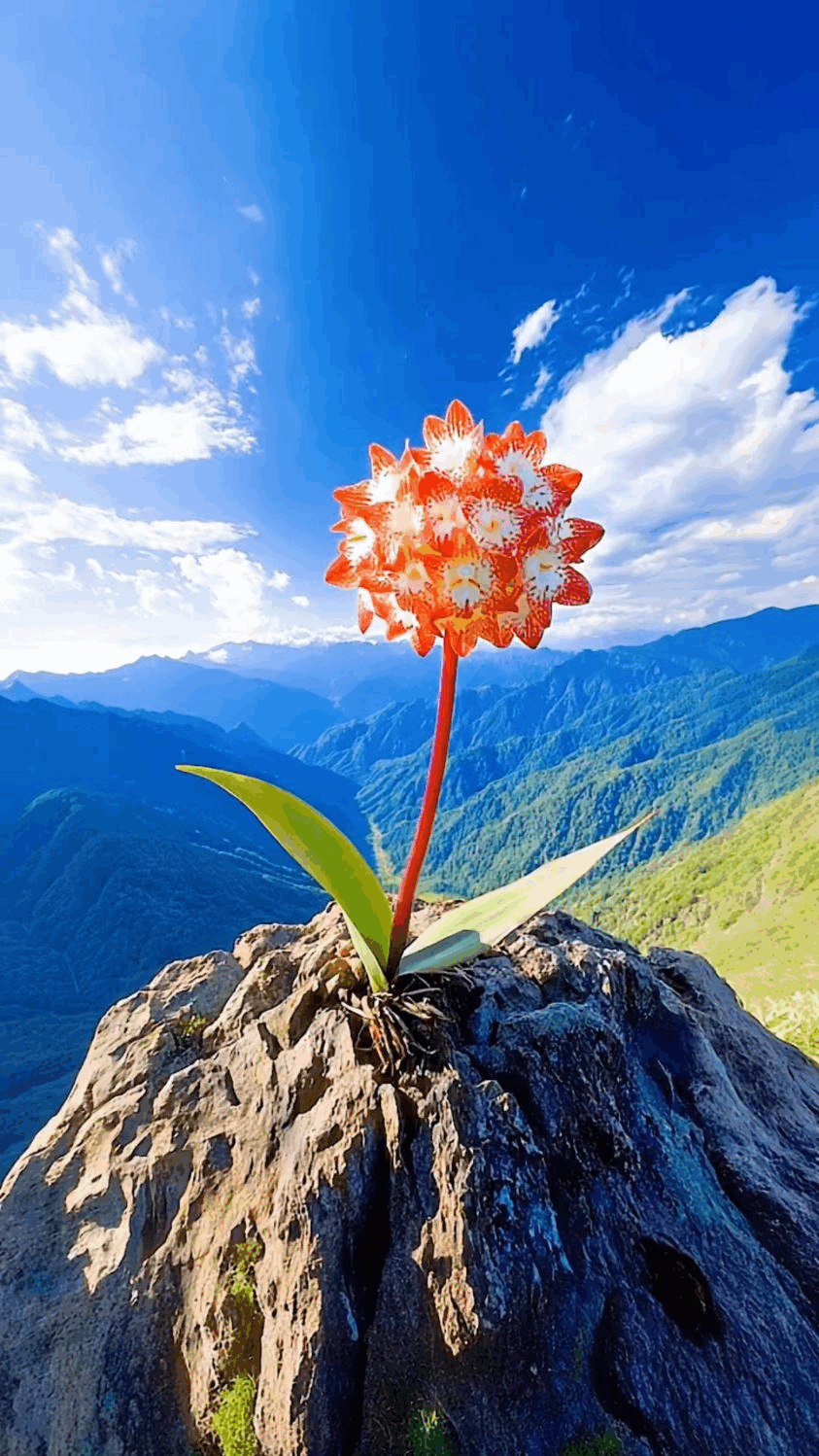
在当下诗歌写作场域中,多元化态势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景观,每位写作者似乎都在竭力构筑独属的风格标识,却也伴随着对异质风格的认知隔阂。即便如此,诗坛对一线名家的创作范式仍保持着相对包容的态度,而基层诗歌爱好者的作品往往因缺乏鲜明的个性印记,难以获得广泛的认同性。湖北孝感安陆的诗歌爱好者陈宗平便身处这样的创作语境中,作为与其相识十余年的同城诗歌爱好者,我见证了他从诗歌交流到风格成型的完整历程。他的写作路径始终带着“野生圈子”的鲜明烙印——那些由业余爱好者构成的非体制化创作社群,虽缺乏专业理论的系统滋养,却为他提供了自由生长的精神土壤。历经十余年的写作淬炼,他的诗歌已形成独特的美学特质,若以一言蔽之,便是以“野蛮生长”的姿态构筑起自由幻想的乌托邦世界,在当代诗歌的谱系中开辟出别具一格的精神向度。
所谓“野蛮生长”,本质上是对当下诗歌创作中“正统范式”的自觉背离,这种背离可置于福柯“话语权力”理论框架中审视:主流诗坛的“正统性”实为一种被权力规训的话语建构,它通过审美惯性、发表机制等形成隐性规训,将诗歌创作纳入既定的意义生产链条。诗人、诗歌理论家陈超曾尖锐指出某些创作倾向为“成批生产的颂体调性的农耕式庆典”与“中国士大夫的逍遥抒情”,这类写作恰是话语权力规训下的产物,往往陷入权力话语与审美惯性的双重窠臼。反观陈宗平的诗歌,其突破性正体现在对这种“正统性”的解构上——如德里达所言,解构并非否定,而是打破既定的意义链条,暴露话语的裂缝与可能性。
他的写作拒绝成为任何意识形态的注脚,也不屑于迎合主流审美趣味,而是以近乎原生的力量楔入当代生存经验的核心地带。近期读到他发表于“21世纪散文诗歌”公众号的《从细枝到岩石》组诗,其中《过故人居》一诗尤为典型:“桑椹树迎客,横溢的枝干/抚慰着故人的缺席”——诗中“桑树”意象的运用堪称解构主义的生动实践。作为本地人,我深知门前植桑在地方文化中实为禁忌,“桑”与“丧”的谐音关联着不祥的隐喻,风水学更将其视为破败之兆,这一意象在传统话语中早已被固定为“负面符号”。然而诗人却逆习俗而行,让桑树以“迎客”的姿态出现,这种意象的陌生化处理,实则是对传统隐喻链条的断裂与重构,暗含着对乡村衰败的隐喻性书写。诗中“寒塘、棚屋、狗窝/以及零星的鸡埘痕”等物象的并置,共同构建出一幅传统农耕文明消逝后的残破图景。在当下充斥着“乡村振兴”宏大叙事的语境中,陈宗平独独选取记忆中破败的旧村落作为书写对象,这种视角的偏执性恰恰彰显了他对诗歌精神纯粹性的坚守——在布迪厄“文学场域”理论看来,这是基层写作者对“支配性场域”(主流话语、权威审美)的象征性反抗,既流露着对逝去乡村文化的深切眷恋,也完成了对场域权力结构的微末颠覆。
与“野蛮生长”的精神气质相匹配的,是陈宗平极具个性的语言系统。他彻底摒弃了“正统颂体诗”中诸如“鲜花”“火焰”“光芒”等程式化的唯美语汇,转而在诗中大量植入“条石、铁水”(《论古墓打开的特殊方式》)、“淫羊藿、巴戟天”(《春药》)、“棚屋、狗窝”(《过故人居》)等冷硬、粗粝甚至带着野性气息的语素。这些意象的反复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构成了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密码与诗歌内部的运作机制,如罗兰·巴特所言,它们使文本成为“可写文本”——读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需参与意义的生产与重构。
他无意迎合传统读者的阅读期待,而是致力于寻找与自身风格相契合的接受群体。在《过故人居》中,“鸡鸣下酒,鱼获曾挤破盘沿。/病魔付费在途”这样的句子,以撕裂性的语言组合打破日常逻辑,“付费”一词的错位使用,将生命的无常与病痛的侵袭转化为冷峻的交易场景,使词语超越字典义,抵达生存经验的深层维度。这种语言实践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摹写,而是通过意象的暴力拼贴与语义的强行扭转,实现对生存本质的刻骨揭示——这恰是阿多诺“否定辩证法”在诗歌中的体现:拒绝将生存经验纳入同一性的概念框架,而是以破碎、矛盾的形式呈现存在的本真状态,构成了一场尖锐而开阔的精神历险。在他的诗中,每个词语都承载着独特的生命重量,既非传统抒情诗中情感的附庸,也非口语写作中日常经验的直白转述,而是在自由跳跃的语型中,建立起诗歌与具体生存的隐秘联系。
探究陈宗平“野蛮生长”的写作姿态,离不开对其创作生态的考察。他长期活跃于几个由业余诗歌爱好者组成的微信群,这些社群呈现出典型的“野生”特质:写作者们不为发表功利所累,仅以纯粹的自娱自乐为创作动机,在诗歌中肆意释放着对生活的叹息、自恋与斥骂。这种非职业化的写作状态固然赋予了创作极大的自由度,却也在初期暴露出明显的缺陷——写作难度的降低导致部分作品陷入简单化与庸常化,抑制了精神深度的开掘。陈宗平的早期创作亦未能完全摆脱这种局限,这也是他的作品直到后期才偶尔见诸《诗歌月刊》等专业刊物的原因。毕竟在当下诗坛,纸刊发表依然是衡量诗歌水准的重要尺度,“野蛮生长”的写作若想突破圈层壁垒,必须经历更为严苛的审美筛选——这正是布尔迪厄所言“场域斗争”的体现:边缘写作者需在保持自身特质的同时,获得“支配性场域”的象征性认可,方能实现影响力的拓展。
所幸的是,经过十余年的持续写作训练,陈宗平逐渐突破了初期的局限。他在保持“野蛮”特质的同时,日益具备处理复杂经验的能力,能够精准把握生存状态的真实性,使诗歌获得了不可忽视的社会价值。他的语言既非传统抒情诗的形容词堆砌,也非流行的口语化叙事,而是在一种灵活多变的语型中自在游走。当他写下“不是说/非得用地磁、雷达。/条石、铁水、积沙层也有懈怠之时。//用你们的宋词试试,/人立落花、燕飞细雨时,/半阙‘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髭。'/也许管用。”(《论古墓打开的特殊方式》)时,工业物象与时间意象的奇妙嫁接,既保留了生活的质感,又赋予了诗意的超越性——这是海德格尔“诗意栖居”的另类诠释:在技术理性主导的时代,诗歌不必依赖“高雅”意象,日常物象的创造性组合亦可成为存在之真理的显现;而《春药》中“遇到淫羊藿、巴戟天、肉苁蓉,/他便用背包采回来。/以为捣成形容词,/去做壮语的前缀,/便能得到一个满意的句子。/殊不知,这并不是奴家/企盼的家信。”,将中药材的药性与词性本体的更迭并置,在世俗经验与诗意表达之间建立起微妙的张力。这种写作既扎根于具体的生活本体,又向着精神的乌托邦敞开,形成了独特的“诗歌物质”——那是一种基于个人生命体验的语言生成物,既保持着生活的原始肌理,又闪烁着幻想的灵光。
在当代诗歌日益陷入技术主义或观念游戏的困境时,陈宗平的“野蛮生长”提供了一种别样的可能。他的写作证明,即便在非体制化的创作环境中,只要保持对生存的敏锐洞察与语言的探索热情,依然能够构建起独特的诗歌王国。他的乌托邦并非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深深植根于对乡村变迁、生命病痛、日常经验的真切感受,通过那些带着泥土气息与金属质感的词语,他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被主流话语遮蔽的真实世界。这种写作或许缺乏学院派的精致技巧,却有着原生的力量与鲜活的质感,如同荒野中疯长的植物,以不驯的姿态对抗着标准化的审美秩序。从早期的粗糙到后期的成熟,陈宗平的诗歌历程印证了“野蛮生长”的辩证性——它既是对束缚的反抗,也需要在持续的自我淬炼中实现超越。当他的诗歌逐渐获得专业刊物的认可时,我们看到的不是写作锐气的消磨,而是“野蛮”特质与艺术水准的有机融合,这种融合让他的诗歌既保持着个体精神的独立性,又具备了介入现实的美学力量,在当代诗歌的多元格局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作者简介:蒋红平,湖北安陆人,中国作协会员,安陆市作协秘书长。已出版诗集《醉清风》《水的黑眼睛》《福兰线》《黑夜的火车》4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