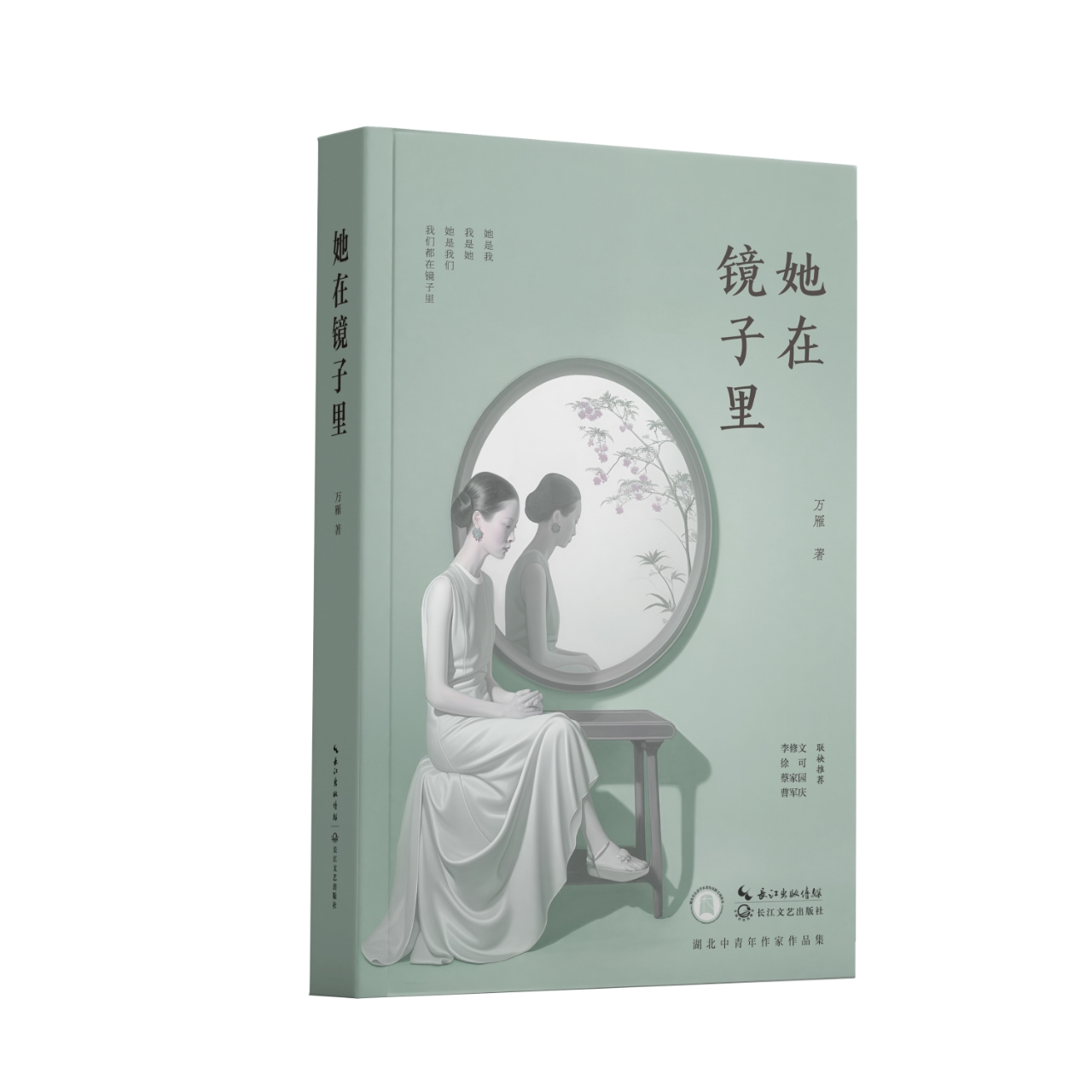
在当代湖北文学的版图中,孝感作家万雁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逐渐崭露头角。她的文学创作之路始于二十年前,最初以散文创作为主,而后将创作重心转向中短篇小说领域。其新作中短篇小说集《她在镜子里》收录《黑色足球》《树上长着馒头》《风流云散》《她在镜子里》《锦缎布缎不断》等9篇作品,以细腻笔触、精巧构思与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洞察,引发读者与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从叙事学与文本分析的理论视角解读万雁近年来的小说创作,能够发现其文本背后潜藏着精妙的叙事策略与艺术编码。这种技术层面的拆解与解密,不仅可以引领读者发现作品阅读过程中易被忽略的精妙之处,更能深入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重新审视那些在常规阅读中匆匆掠过的世相百态,实现对作品更为深刻的感悟。这种解读涵盖小说的语言主题思想、故事选材、悬念设置、隐喻手法、语言风格等多个维度,旨在全方位剖析其创作技巧与艺术魅力。正如罗兰·巴特所言,“文本是一种编织物”,优秀小说往往源于作者生活中的某个瞬间灵感,在将灵感转化为文字之前,作者需要对这一想法进行深入的思考、追问与审视,这一过程赋予了小说精神与灵魂,而后通过技术层面的精心构思,才真正开启创作之旅。
一、悬念构建:叙事张力的拓扑学与意义延宕机制
万雁的小说在叙事结构上展现出卓越的悬念经营能力,这与热奈特提出的“叙事时序”理论形成有趣呼应。她的作品视角极为开阔,充满强烈的生活实感,而最为擅长的便是为故事情节与人物巧妙制造悬念。在其作品中,悬念手法的运用极为普遍,大悬念与小悬念相互交织、层层嵌套,构建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悬念体系,使得故事中的人物、场景、细节以及背后的逻辑变得扑朔迷离、引人入胜。这种悬念设置不仅是简单的情节技巧,更是通过叙事时序的错置、因果链的隐匿,形成类似于拓扑学中的多维叙事空间。
在短篇小说《风流云散》中,万雁运用“预叙”与“悬置”的双重策略。从主角名字中的“香”字,到对香姐“芳香姐爱美成痴,美衣如山,是个行走的衣服架”的介绍,再到小说题目“风流云散”中“风流”二字引发的遐想,一系列元素共同勾起读者对香姐形象与故事的好奇。这种叙事策略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陌生化”效果,通过对人物符号的偏离式编码,打破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短篇小说《她在镜子里》则以几个年轻人夜晚进行的充满魔幻、恐怖色彩的卡牌游戏开篇,迅速引出主角嘉荣的镜子恐怖症,成功营造出紧张刺激的氛围,吸引读者探究背后的原因。这里的“突转式开场”符合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对悲剧情节的要求,通过强烈的戏剧冲突将读者瞬间卷入叙事漩涡。
万雁小说的悬念与逻辑性紧密相连,设计悬念必然需要后续合理的逻辑来解码。她的小说悬念与逻辑性都极为出色,并且往往在悬念揭开时,带给读者意想不到的震撼与内心触动。在《风流云散》中,随着故事的推进,读者会发现主角芳香姐并非如名字和初始介绍所暗示的那样是个风流之人,她的爱美实则源于对生活的炽热热爱与内心世界的良善。这种“解述”过程暗合叙事学中“真相延迟披露”的经典范式,通过不断累积的叙事谜题,最终实现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颠覆”,让读者在认知落差中获得审美愉悦。
二、选材与背景:地方性知识的诗学转译与社会文本互涉
万雁的小说主要以当下中小城市普通人群的生活为背景展开故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题材丰富多样,大多聚焦于底层生活的家长里短,通过这些平凡琐事揭示人性与人心的问题,展现大千世界的真善美。受生活环境的影响,她的小说带有明显的地级市当代城市生活痕迹,这种独特的地域背景使其作品既不同于曹军庆早期以县级市为背景的小说,也与喻长亮的乡村小说有所区别。地级市有着独特的人群生活脉络,既不同于乡村的质朴,也不同于县级市的相对单一,更不同于武汉等大都市的繁华与多元。然而,这一地域特点并未限制万雁小说的视野,她巧妙地从个体情感的私人领域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图景,深入探索普遍的人性命题,在地域特色与普遍关怀之间找到了精妙的平衡点,使小说内容更加丰富立体,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与时代性。
从空间批评理论视角来看,地级市这一特定场域构成了独特的“文学地理学”样本。万雁在小说中对机关公务员、教师、医生等等不同职业群体的书写,实际上是对福柯所说的“异托邦”空间的文学重构。以短篇小说《黑色足球》为例,其选材聚焦于当下社会的单亲家庭,讲述了临近高考的高三学生晓宇晚上在校园被飞来的足球伤及阴部后,日常生活及学习受到严重影响的一系列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包含了母亲对孩子的深厚情感、学校面对事件的态度,以及通过单亲母子关系展现出儿子晓宇善良的性格。作者通过这一故事,展现了对个体情感的入微体察,表达了对时代问题的深刻叩问,同时也褒扬了现实生活中像晓宇这样的人群所具备的传统美德,描绘出一幅属于这个时代的单亲高中生的文学风景。
这种地方性知识的书写,在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理论框架下,实则是对当代社会转型期集体经验的诗学转译。万雁小说中对电诈(《布局》)、卡牌游戏(《她在镜子里》)等新事物的捕捉,不仅是对鲍德里亚所说的“符号狂欢”的文学回应,更构建起与社会文本的深层互涉关系。她以自身的个体生命体验、时代感受和社会经历为出发点,深入思考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时代背景,试图探索解决时代、群体与个体困境及其问题的可能性路径。
三、主题基调:存在主义困境与救赎美学的辩证书写
万雁小说的“暖色调”是其显著特征之一,这种暖色调主要体现在故事往往以令人压抑、伤感、悲悯的情绪开篇,而后情节峰回路转,最终以暖心的结局收尾。读者能够从丰富的人物场景和细节背后,感受到作者追求纯真、良善的内心境界,体会到作者对完美结局的期许。在当下这个后现代式的短暂、喧嚣、功利性流行的时代,这种“暖色”的追求显得尤为珍贵,或许能够成为当下文学回归历史波涛中的中流砥柱。在伊瑟尔的“召唤结构”理论中,这种叙事结构构成了文本的开放性阐释空间,邀请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填补意义空白。
然而,她的作品中也有少数如《双生花》这样反映社会最底层人生存状况的小说,结尾令人深思,读后给人较为沉重的感受。这种冷暖交织的主题基调,展现出万雁对现实生活复杂性的深刻认知。万雁以中短篇为主的创作选择,与其女性书写视角形成互文关系,既避免了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陷阱,又通过微观叙事实现了利奥塔所说的“异教主义”表达,在个体情感与社会图景之间建立起精妙的平衡。这种创作方式,使得她的小说在展现个人情感的同时,也折射出广阔的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
四、隐喻艺术:符号的能指滑动与意识形态解码
万雁在小说题目命名及小说人物名的设置上,巧妙运用隐喻手法,使文字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深意,展现出对拉康“镜像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在《风流云散》中,小说题目及人物香姐看似隐喻着一个风流女子,实则通过反向隐喻,讲述了内心善良、命途多舛的社会底层女子的故事,这种反差增强了故事的戏剧性和感染力。这种命名策略类似于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询唤”,通过语言符号对读者进行无意识的意义灌输。
在《她在镜子里》中,题目隐喻着故事主角是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人。人物“桃潭”的名字隐喻她的心机之深,也暗示其内心会因此产生不安、焦虑、抑郁等情绪。人物“山寨黎明”隐喻此人有着与黎明差不多的外表,实则是一个小心眼、非常自私的人。这些隐喻的运用,使文本成为詹姆逊所说的“政治无意识”的载体,通过符号的能指滑动,实现对社会权力结构的隐性批判。这些作者刻意设计的隐喻,读起来却非常自然,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经过了煞费苦心的揣摩、斟酌和巧思,在文本呈现上达到了举重若轻的效果。文学创作依赖于作家内在的深入思考,需要作者具备稳定且强大的创作内核,只有当作品真正被读者阅读、思考和回味,才能实现文学的意义。
五、语言风格:兼具散文美感的叙事艺术与复调叙事建构
万雁小说的语言刻画细腻、生动,具有鲜明的“跨文类”特征,将散文美学转化为小说叙事的诗性资源。她对语言进行精雕细琢,在每一部作品中都展现出对语言层面的精彩探索,使作品在叙事风格上呈现出多样与统一的特点。这种语言实验在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框架下,实现了不同文类符号系统的创造性融合。
在《锦缎布缎不断》中,以主角云晓月受到电话骚扰起笔,由此引出青年男女婚姻因父母传统观念不同而遭遇阻力,进而发生一系列惊险故事,最终以喜剧收笔。整个故事叙述流畅,语言生动地展现了人物之间的矛盾与情感变化。《双生花》将目光投向青春与生存的层面,以官家女艾紫若与社会最底层女孩赛冰冰在驾校一起短暂学习的交集为切入点,通过细腻的语言讲述底层人群生存的艰难。作者用生动的笔触描绘赛冰冰虽然人长得漂亮,但因家庭贫困、恋爱遇人不淑,再加上父母生病等多重打击而精神失常的过程,深刻揭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同于作者日常的书写风格,《她在镜子里》以恐怖诡异的语言场景开篇,通过渲染氛围,制造出紧张刺激的画面,极大地吸引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使读者迫不及待地想要继续读下去。短篇小说《全家福》则以宁静而细腻的笔触,描绘老爷子八十岁生日时,围绕拍一张新的全家福,在养女与奶奶、亲生子女间产生的复杂微妙的情感牵绊。其叙事如同水墨画般,将养女长期以来与养父母在精神上的对抗以及最终和解的过程,层次清晰地描摹出来。这种“水墨叙事”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化,更在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意义上,构建起多重声音的对话空间。
万雁的小说拥有独特的语言韵律与印记,其叙事语言结构顺畅、明朗。在一个个基本线性却又波澜起伏的故事设置中,她构建起属于自己写作个性的复调式和谐叙事风格。这种风格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既能感受到故事的连贯性,又能体会到情节的丰富变化,沉浸于她所创造的文学世界之中,实现了本雅明所说的“讲故事的人”的现代转型。
六、人物群像:精神分析视域下的自我救赎与主体建构
在万雁的小说中,塑造了诸多不同类别的人物群像,这些人物往往有着人性的弱点,他们内心的“小”,可能表现为对他人的“小心眼”,也可能体现为自身精神上的焦虑、抑郁等症状,而这些问题常常成为小说中的主要故事点。从精神分析视角来看,这些人物的困境与挣扎,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
在《她在镜子里》中,嘉荣因小时候对同学造谣诋毁,内心充满愧疚,这一过往经历给她后来的生活带来了失眠、焦虑、抑郁等精神症状。在与他人进行“真心话”游戏活动时,她将内心的秘密倾诉出来,从而实现了内心精神压力的释放,完成了一次自我救赎。这种情节设置暗合弗洛伊德“创伤—宣泄”理论,通过叙事机制实现人物的心理疗愈。
《锦缎布缎不断》中,云晓月春节前往男友家,却因男友母亲的封建迷信观念,导致婚事受阻。随后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如男友去追云晓月造成车祸、男友母亲晕死等,经过这场生死变故,男友母亲最终改变想法,同意了两人的婚事,人物关系在冲突与和解中得到转变,也体现了一种观念上的自我救赎。这种情节发展展现了人物在面对生活重大事件时的思想转变,反映了人性中宽容与理解的力量。
在《风流云散》中,香姐在自身并不富裕的情况下,长年资助一个因车祸失去双亲、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孩子。深入探究会发现,这是因为香姐老公当年疲劳驾驶引发惨重车祸,香姐以此方式赎罪,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实现了内心的救赎。这一情节体现了人物通过自我牺牲和奉献来寻求内心平静的心理过程,展现了人性中善良与救赎的美好品质。
《黑色足球》中,晓宇在明知是他人踢的足球砸伤自己的情况下,选择不说出来,他的善良不仅展现了人性的美好,也让母亲白梅明白了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善良,这一情节使人物在情感与认知上都得到了升华,体现了对善良品质的珍视与弘扬。这种人物之间的情感互动和思想转变,丰富了小说的主题内涵,引发读者对人性的深入思考。
与上述故事中人物的救赎方式不同,短篇小说《树上长着馒头》(又名《玉兰花开时》,刊发于《长城》2025年第4期)中的简凤得到救赎的过程别具特色。简凤是国企老总太太,三十多岁便“病退”在家,在丈夫临近退休时突然离世后,她的生活瞬间崩塌,陷入抑郁之中。妹妹简凰让她搬回年轻时单位的老房子,在这里,她遇到了邻居小连——一个年轻的肾衰竭长期透析患者,小连的老公下岗后从事在外给挖掘机送油工作,却在一次交通事故中身亡。在与小连的日常生活接触中,简凤看到了社会底层生活更为艰难的一群人,他们面对困境时展现出的豁达与向上的精神,深深触动了简凤,以及简凤对小连日常生活的无私帮助过程中,使简凤内心世界得到荡涤,精神上逐渐释怀与开朗,完成了自我救赎。在拉康“镜像阶段”理论视角下,简凤的转变可视为主体认知结构的重构,她通过与社会底层人物的相遇及对他人的帮助,完成了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这种“他者镜像”的引入,打破了原有封闭的主体认知系统,实现了精神层面的突围。
《全家福》中,阳阳的大姑妈因得知自己不是亲生的,不愿与养父母一家人来往,心中始终存在一个“结”,导致郁郁寡欢。在老爷子八十岁生日时,她回家看到新拍的全家福没有自己,便匆匆离开,后来甚至得了严重抑郁症到北京住院治疗。这一人物的经历反映了家庭关系中的复杂情感以及人物在心理上的挣扎,也从侧面展现了人物在困境中寻求内心解脱的过程。
万雁始终聚焦于现实生活中卑微的小人物,她以细腻的文字记录周围世界日常生活所带来的情感触动,将自己敏感温柔的内心世界融入笔端,期望能够在尘世的悲怆之处投射出一丝光芒,给予读者温暖与力量,同时也引发读者对生活、人性的深入思考。通过对万雁中短篇小说集《她在镜子里》多个维度的技术性拆解与解密探讨,我们不仅能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她的创作特色与艺术成就,也得以窥见当代文学在个体经验与社会现实之间搭建的桥梁,以及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救赎方式的永恒价值。
作者简介:蒋红平,湖北安陆人,中国作协会员,安陆市作协秘书长。已出版诗集《醉清风》《水的黑眼睛》《福兰线》《黑夜的火车》4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