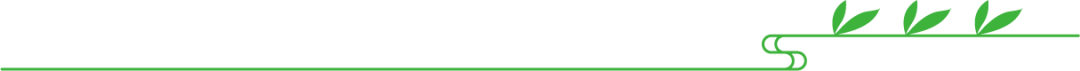www.chufengwang.cn

万雁发表于《西部》2025年1期头题的小说《她在镜子里》,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内核,构建起关于人与人性的深刻探讨。依据杰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小说通过构建存在主义式的双重时空结构,将现实与超现实并置,实现了对线性历史观的解构。由于人性的复杂多面,小说呈现出两条并行的生活脉络:一条是人类因对诸多生活未知的认知不足,构建出充满魔幻神性色彩的世界,由此滋生内心的焦虑与恐惧;另一条则是当事物真相逐渐揭开后,内心恐惧得以缓解与消散的过程。这种时空的断裂与交错,恰似拉康“镜像理论”中主体认知自我的过程——镜面不仅是物理反射的媒介,更成为主体认知自我的重要他者,而嘉荣在当代场景中反复遭遇的镜面恐惧,实则是历史创伤记忆在镜像场域中的无意识复现,形成德勒兹意义上的“时间晶体”。
从艺术表现来看,小说开篇以富有诗意的语言描绘故事场景,“野奢酒店外观呈葱绿色,蘑菇造型,木石结构,蹲于林木蓊郁的半山腰,散发出一种蓄意隐遁的气息。当夜暮四合、灯光亮起时,透过枝叶掩映的雕花仿古窗,可见七八个衣衫单薄的男女围坐一圈。”这种疏离的全知视角如同上帝之眼,将年轻群体的亚文化场景客观呈现,营造出存在主义式的荒诞氛围,暗合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询唤”的机制。而这种叙事策略,也正如巴赫金式的复调结构,让不同时空的声音在文本中展开对话,解构着传统的权威叙事。
故事从七八个年轻人玩的卡牌游戏写起,其中一人连续五次抽到“普通人”,营造出神秘诡异的氛围,紧紧抓住读者的心。这种开篇方式,恰似将读者抛入加缪笔下的荒诞世界,在无序中寻找意义。比如“‘法官'将嫩绿枝条朝外一甩,拖着瘆人的长音发出指令:‘天——黑——了,大——家——请——闭——眼——'”,这种诡异感让读者既困惑又欲罢不能,成为推动读者继续阅读的重要因素,也体现了叙事对读者心理的“询唤”作用。之后主角讲述的镜子诡异故事,作者设置的叙事陷阱进一步引发读者的阅读期待,而最终揭晓的谜底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完成了对读者认知的“陌生化”与“再熟悉”过程。
小说第一、二节采用第三人称叙述,由于此时尚未涉及小说主题思想的核心表达,所以活动中的人物都以各自的外貌特征作为指代,先后出现穿烟灰T恤的男生、韩式齐刘海的女生、戴沉香手串的男生、烫炸毛头的男生等,直到主角“嘉荣”出场才有了姓名。这种叙述视角的选择,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策略,以客观视角构建起故事的荒诞底色。“嘉荣”这个名字颇具特点,既像男生名又像女生名,其背后的特殊含义也给读者留下悬念,恰似文本中的“空白点”,等待读者进行伊瑟尔所说的“召唤结构”式解读。很快,“其实,她早就如坐针毡,只是碍于时机一直未离开。”一句表明主角是女性。随后小说解释“嘉荣”二字源于《山海经》中的一种仙草,这也是主角喜爱的上古奇书,一同玩闹的青年男女还喊她绰号“仙草”。小说中这些装扮奇异的人物聚集在一起,不仅让读者心生疑惑,还增添了恐怖氛围,构建起本雅明所说的“灵韵”消逝后的现代荒诞景观。而后逐步介绍男女青年文艺、非主流的打扮,并在第二节“这是在山城开办的一期编导培训班,时长一年半,班上五十余名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学员身份多为导演、演员、编辑和编剧。”解释了人物装扮及族群存在的合理性与小说逻辑,使小说的氛围从恐怖玄幻的魔幻色彩向现实大众生活过渡,完成了叙事时空的“缝合”。小说特意提到戴沉香手串的人眼睛不近视却总戴平光眼镜,这既增强了故事的恐怖诡异感,也为后文主角嘉荣的“镜子恐怖症”埋下伏笔,形成叙事上的“预叙”结构。另一方面,当代年轻族群的非主流装扮,如戴鼻钉、留长须、扎脏辫、穿乞丐裤、二次元风格等,他们所处时代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卡牌游戏、拥有上亿用户的女性专属APP预测“姨妈”、人们常见的焦虑抑郁等精神症状这些新鲜事物,充分展现了时代的快速发展,与后文讲述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故事形成精神与物质层面的巨大时代落差,这种对照恰似杰姆逊论述的后现代文化中时间深度感的消失,两种时空在文本中形成量子纠缠般的对话关系。
小说从青年人的“卡牌游戏”到“真心话大冒险”,从“玄幻故事”到主角心理上的“镜子阴影”,逐步展开情节进入第三节。到了第三节,作者转换叙述角度,采用第一人称,这种视角的嬗变正如阿尔都塞所言,完成了叙述者从“他者”到“主体”的意识形态转变,增强了故事的现场感与表达的流畅性,也构成了本雅明所说的“经验的救赎”。故事直接回溯到“我”十一二岁时,“我”妈辞去小镇麻油厂的工作,把“我”送到乡下外婆家,然后带着总是流鼻涕的弟弟去广东投奔“我”爸,清晰地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大批工厂改制、大量工人下岗的特殊社会时期,社会观念与精神思潮在物质贫乏的环境下急剧动荡与转变,讲述了小说主角这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从与妈妈生活的小镇来到乡下“槐花村”与外婆生活后发生的故事,构建起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交织的叙事空间。
和学生时代大多数少男少女一样,作为同学,玩得好的三个小女生效仿武侠故事中义结金兰的仪式成为死党,并各自取了化名。故事呈现出较为典型的学生生活形态,所以三个学生以“桃花、桃潭、桃水”为化名出现,除了前文提到主角嘉荣是“桃潭”外,“桃花”“桃水”的真实姓名并未交代,这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写作手法,形成叙事中的“空缺”,引发读者的阐释欲望。将“桃潭”之名赋予主角嘉荣,与后文内容也有着特殊寓意,这种命名方式暗含着符号的象征暴力。虽然“桃潭”这个名字是通过扔纸条最后挑选得到的,主角虽不满意却以自嘲的方式接受,认为“潭多有包容性,任尔花容月貌、水碧山青,不过是花自飘零水自流,唯潭恒久远,花也好,水也罢,潭皆能装载。”然而从后文故事来看,主角嘉荣并不具备包容的个性,且后来因内心的自责、悔恨,导致成年后一直处于精神焦虑、抑郁、敏感的状态,形成了文本内部的反讽张力,印证了保罗·德曼的修辞性阅读理论——语言的字面意义与实际意义的断裂。而“桃花”这个化名,似乎和日常生活中带有贬义的“桃花运”类似,预示着她悲剧的命运,也为后文故事发展埋下伏笔,构成热奈特所说的“预告”叙事策略。
文中交代三人因都“爱臭美”而玩在一起,和许多青春期爱美的少女一样,她们喜欢照镜子、看帅哥,由此引出后续关于寻看帅哥同学、在桃水家留宿,以及留宿当晚发生的蝴蝶发卡丢失和镜子无故被打碎的故事。从小说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情节可以看出,作者写作手法娴熟,语言简练且逻辑性强。而在这一过程中,“蝴蝶发卡”与“美颜镜”构成了福柯式的权力装置,当美发店老板以商品所有权对未成年少女进行道德审判时,物质符号异化为规训工具,完成了对主体的符号暴力。这种暴力通过语言的污名化(如“小偷”标签)与经济惩罚(共同赔偿),在少女的精神世界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实质是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中社会资本在微观层面的运作,将个体的偶然过失转化为影响终身的社会烙印。
小说中另一个对故事走向影响重大的人物,是租桃水家一楼做美发生意的小伙“山寨黎明”,和前面所有角色一样,他也只有作者赋予的代号——小女生们起的绰号。这个帅小伙长得酷似香港“四大天王”中的黎明,发型是蓬松有型的三七分。从与美发小伙相关的故事开端,很难看出他性格狭隘的一面,但从故事结局能够明白作者给他起“山寨黎明”这个化名的深层隐喻,即该美发小伙远没有“四大天王”中黎明那般大气、良善的胸怀与精神境界,这种命名策略构成了巴特所说的“符号的神话化”过程,通过能指的替换揭示所指的本质。
小说中的重要道具是美发店的美颜镜子,类似现在的“哈哈镜”,能把人照得显瘦,让姑娘们十分喜爱。和那个年代开小店的普通人一样,美发小伙除了美发还售卖一些小饰品,如耳环、发卡、头花、手链等,这些都是小姑娘们的心头好。随之,故事中的“蝴蝶发卡”与“美颜镜”成为引发事端的根源。在桃水家留宿那天,美发小伙刚进了漂亮的发卡,三人对一枚镶钻的“蝴蝶发卡”十分着迷,可没钱购买,那个年代小孩子身上基本没有零花钱,只能看看。而桃花却像着了魔一般,说“如果戴上这枚蝴蝶发卡,是不是就会有男生喜欢?”。接着,桃花半夜以一起上厕所为由,拉“我”去偷偷看一楼美发店柜台中的那枚蝴蝶发卡,随后莫名发生了美发店“美颜镜”摔碎、蝴蝶发卡失踪的诡异事件。事情发生后,长得像黎明的美发帅哥露出真面目,咆哮着“偷了蝴蝶发卡就罢了,干吗还要毁我的镜子,这是谁干的?心肠太坏了!”——“山寨黎明”步步紧逼,让“我”俩走投无路,原本以为他长得帅,“我们”又年纪小,他或许会网开一面,没想到如此狠心……再看他那三七分发型,哪有什么蓬松有型,分明像一团乌云、一坨牛屎。因为事件诡异,“我”和桃花都成了被怀疑的小偷对象,在“我”与桃花各自辩解时,“我”想起不久前关于自己父母关系异常的谣言——是桃花妈传给桃水妈的,一时邪念丛生,“我”冲着桃花说:“你说上厕所,可又不上,原来是为了偷发卡。既然偷了,就承认呀,给叔叔道个歉,叔叔人帅心好,肯定会原谅你的。”在这一系列情节中,符号暴力的运作机制得以充分展现,语言成为伤害他人的利器,也完成了对主体间关系的重新建构。
事件的结局是“我”和桃花各赔偿一半的钱,“三人帮”的死党关系也破裂,如同少年版的“三国”。后来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桃花辍学回家,而“我”从外婆口中得知父母关系异常的谣言是真的——想到“我”爸……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滴落在绣有“花好月圆”图案的橘红枕巾上。也就是从那晚开始,“我”感觉自己内心发生了某种难以言说的变化,和以前不一样了。这种个体内心的变化,实则是符号暴力对主体精神世界的深度入侵,导致主体认知与情感的异化。
多年后回到槐花村,“我”弟弟已从流鼻涕的小孩长成一米八的大小伙,桃水结了婚又离了,常住娘家,俨然成了额头有白发的农村中年妇女。桃水告诉“我”,她后来只见过桃花一次。桃花十八岁就嫁人了,听说为了彩礼,又因为被贴上“小偷”标签名声受损,被逼嫁给外地一个开砖窑厂的矮小男人。后来砖窑厂被关停,男人染上毒瘾,毒瘾发作时将她打流产,导致她丧失生育能力,男人也进了戒毒所。之后,桃水也再没见过桃花。桃花的悲剧命运,是符号暴力导致主体异化的极端体现,印证了齐泽克所说的意识形态对个体的“询唤”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在那次桃水与桃花的见面中,桃花反复跟桃水说,那天晚上她真的没偷发卡,只是拿出来看了一眼,好像也没碰到镜子。还说,她真的很想“我”,很怀念以前快乐美好的时光,做梦总梦见“我”——这让“我”内心深受触动,充满自责。同时桃水还告诉“我”,在桃水家堂屋供桌底下——曾经的美发店发现一个拳头大小的老鼠洞,洞里有那枚已经变色的蝴蝶发卡,“听到这里,我小声嘟囔着‘都怪老鼠’‘都是老鼠惹的祸’”,心中满是震惊、自责与难受,还不自觉地为自己的错误找理由。这种心理反应,体现了个体在面对历史真相时的自我防御机制,也暗示着救赎之路的艰难。
进入小说第七节,故事又回到开头年轻人晚上游戏的现场,作者重新采用第三人称叙事。以当代青年人的认知,穿烟灰T恤的人马上推测出嘉荣故事中那面具有美颜功效的镜子是嘉荣在慌乱中不小心撞碎的,并大胆猜测“桃花是小偷”的恶名是嘉荣散播出去的,这才造成桃花一生的不幸,所以嘉荣才一直被严重的心理阴影困扰。当她面对镜子时,尤其是能清晰照出人像的镜子,反应会更强烈,“她恍惚看见镜中有人影晃动,那不是她自己,而是一个五官模糊、面色苍白的女人,有时还会发出瘆人的声音,像是哭,又像是笑。倘若将这些症状归结为幻视、幻听,那么这种情况已伴随她多年。此外,她还出现入睡困难、多梦、早醒等睡眠障碍。”这些充分反映出主人翁嘉荣严重的焦虑、抑郁等精神症状,构成了存在主义式的精神困境——个体被过去的阴影所困,无法在当下获得真正的自由。
文章结尾,几个年轻人帮嘉荣出主意,想通过角色扮演游戏,以教堂式忏悔来消除她心中的自责,以及“上天的惩罚”“苦不堪言、难获安宁”“睡眠障碍”等精神问题,或者像麦克尤恩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赎罪》中的布莱欧妮一样,将自己所犯过错写成小说,以此弥补谎言、澄清事实,寻求宽恕与救赎。但扮演女法官的人说“你们真的认为一个剧本就能弥补谎言造成的伤害吗?于桃花而言,她的生活,她的人生,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她对这些一无所知,冤案并未昭雪,真相并未大白于天下,真正的赎罪只有通过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寻求被伤害者的原谅才能得以实现,而不是仅凭一个剧本就能完成的。”立即否定了这种想法,引发众人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只有找到失踪的桃花,嘉荣才有可能获得受害者的原谅,实现精神解脱。这种情节设置,恰似鲍德里亚所说的“拟像狂欢”,当年轻群体试图通过戏剧化的表演实现精神救赎时,实则陷入了利奥塔笔下的“元叙事危机”,暴露出后现代社会精神救赎的虚假性,印证了齐泽克的观点:当代人在符号系统中寻求救赎,本质上是对真实创伤的再度逃避。随着宿管在外面大喊时间太晚,让这群夜猫子别吵了,众人纷纷散去。嘉荣回到自己房间,在镜子中看到自己不再紧致、饱满的脸上写着平静和松弛,小说至此结束。嘉荣似乎在这个夜晚与朋友的真诚交流中,在心理和精神上达到了某种宁静。然而,这种平静与其说是真正的救赎,不如看作是存在主义式的“向死而生”——在认清救赎不可能的前提下,获得的某种荒诞的自由。
《她在镜子里》通过镜像符号的多重指涉、叙事视角的解构性运用,构建起关于人性异化与救赎的后现代寓言。小说不仅是对个体创伤的书写,更是对整个时代精神困境的症候式分析。在消费主义盛行、精神信仰式微的当下,万雁的创作提醒我们:真正的救赎或许不在于寻找外在的解决方案,而在于直面镜像背后那个伤痕累累却依然真实的自我。这种存在主义式的勇气,正是当代文学应当传递的精神力量。
作者简介:蒋红平,湖北安陆人,中国作协会员,安陆市作协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