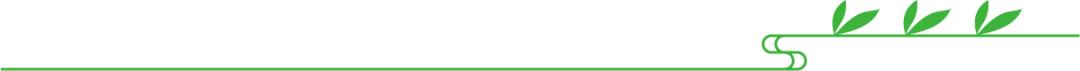乡间有句谚语,滑不过黄鳝精不过鳖。可有个叫老憨的人,却偏偏是鳖精的克星。
老憨捉鳖很独特,到了一方池塘,先拿眼逡巡一周,有鳖无鳖,便了然于胸。瞅准了,就扛起“扣盆”,下到塘中。这扣盆用木板箍成,形如脸盆,深似水桶,中间置有一柄。老憨在水中立定后,先在掌心吐口唾沫,然后一搓,便把扣盆高高抡起,呼啸着扣在水面:嗵!这极具穿透力的一声闷响,在天性胆小喜静的鳖听来,无疑就是一声霹雳。于是,惶恐之下,那鳖便拼命地往淤泥里钻去。这一钻,一串串气泡就咕嘟嘟地翻腾到水面。老憨一见,便水蛇般的游过去,把手中的鱼叉往气泡下一叉,然后一个猛子扎下去,在鱼叉四周的淤泥里,拿手一摸,一抠,一只四爪乱弹的老鳖,便成了老憨的囊中之物。
靠着这手捉鳖绝活,没爹没妈的老憨,日子照样过得有滋有味。28岁那年,老憨还亮了更绝的一手,竟然拿两只鳖换回一个媳妇来。
那天,老憨去了几十里外的山村捉鳖,远远地看见了一口大塘,没等他走过去,就听见扑通一声。老憨还以为有人洗澡哩,可一走近,水里没人,只有一缕长发隐约可见。老憨慌了神,把工具一扔,就跳了下去……
老憨把姑娘送到家后,才从她母亲口中得知,姑娘打小就体弱多病,上不得田下不得地。嫂子来家后,就对着她比鸡骂狗,翻白眼珠子。姑娘实在怄不过,就想一死了之。老憨听了,把笆篓里的两只鳖往地上一倒说:留给你女儿补补身子吧……
就是这两只鳖,一下子打动了娘俩的心。
结婚那天,村里人打趣道:你老憨鳖了这么多年,从今儿起,就不用再“憋”了。
看着弱不禁风的媳妇,老憨就想,三十年的老鳖百年的参,这都是养人的好东西,给媳妇多补补,一定错不了。老憨他先拿几年的嫩鳖给媳妇温补。过了一段,再拿五年以上的成年鳖滋补。最后,就拿上十年老鳖大补。经过老憨这一番调理,原本干皮巴拉的病婆娘,几年下来,便滋润成丰腴水灵的俏娘们了。一村的男人,眼睛瞅着,心里像有鳖爪在挠。
媳妇的病好了,可老憨却添了块心病:这年头,田都没人种了,水塘自然无人管理,堤垮了,水干了,鳖就成了没娘的娃。再加上水里土里,到处残留着农药,让生性娇气的鳖更是雪上加霜。这鳖越来越少,可吃鳖的人却越来越多,鳖价自然是一路疯涨。于是,便有人拿着一瓶“鳖扫光”,见水就往里面倒。不消一个时辰,那鳖的祖宗八代,便全都漂上来集合了……
这一来,老憨这个捉鳖大王不得不背起行李,远走他乡去打工。也许是前世与鳖有缘,一个偶然的机会,老憨进了一家养鳖场。到了这里,老憨才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自己的捉鳖手艺算个啥,人家这养鳖技术才叫一个绝:酒盅大的鳖仔,饲料一喂,就像吹气球似的,一天一个样……老憨虽然没上过学,却有鳖样的灵性,很快,他就掌握了全套的养鳖技术,然后,行李一背,兴冲冲地回了家。
没过几年,老憨就发了,盖起了楼房,开上了小车,曾经的捉鳖大王,又成了响当当的养鳖大王了。看着给自己带来好运的老鳖,老憨都想喊它一声“老爹”了。
不过,有人喊老憨“老爹”却是真的。结婚以后,媳妇模样天天变,可肚皮却一直没有变。直到养鳖发财那年,一下子双喜临门。于是,那池中的宝贝鳖,便成了宝贝女儿的最佳营养品了:红烧鳖,清蒸鳖,清炖鳖……望着女儿的模样,老憨别提多高兴。你看那手,那腿,胖乎乎的,藕节似的,就像年画中的娃娃一般,看着就喜气。
渐渐地,当妈的发现,自家的女儿吃好的喝好的,咋还比村里同龄孩子矮一截呢?老憨说,没事,咱俩都人长腿长胳膊的,孩子长个还不是早晚的事。
一天,当妈的给女儿洗澡时,突然发现六岁孩子,胸脯竟然鼓了起来。老憨愣了一下,想了想,又笑了:这说明咱家孩子营养好啊。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老憨再也坐不住了。七岁的女儿竟然见红了,把裤子都洇了一大片。
夫妻俩带着女儿,开车直奔省城。
医生检查后,皱着眉头问:你们给孩子吃了什么药?
老憨大惊:我的孩子健康着哩,没吃啥药啊?
问着问着,医生一拍桌子,厉声道:还说没有,给孩子吃那么多甲鱼,不等于给她吃药吗?
夫妻俩面面相觑,啥?你说啥?!
医生也愣住了:你们养甲鱼,难道不知道饲料含有啥成分?
老憨还在迷糊:俺啥没啥文化,只晓得喂鳖长得快。可俺给孩子吃的是鳖,又不是饲料?
医生叹口气,说,现在的速成饲料中,都含有各种激素。你的孩子摄入了甲鱼中残留激素后,就造成了现在的发育异常。这种病的后果是,发育提前成熟,骨骺提前闭合。严重的,还会影响智力发育,以及其它无法预知的后果……
老憨撕扯着头发,半天才嚎了一声:王八蛋啊……
听说老憨从省城回来了,马上有人登门要货。可“鳖”字刚出口,老憨就一脸的杀气地吼道:滚!那模样,就像只红了眼的鳖,逮谁都想咬一口。

《鳖殇》:自然之殇与现代化陷阱中的伦理困境
朱道能的小说《鳖殇》以乡村捉鳖人老憨的命运起伏为主线,通过甲鱼这一象征物,编织了一个关于传统与现代、自然与异化的寓言。作品以平实的语言和细腻的笔触,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及其反噬,同时深刻叩问了科技伦理与人性贪婪的边界。在乡土中国的背景下,作者以老憨一家三代的悲剧,映射出整个时代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
一、自然与人的共生:传统技艺的双重性
老憨的捉鳖绝活被乡民称为“鳖精的克星”,这一设定暗含了人与自然既依存又对抗的复杂关系。小说开篇的谚语“滑不过黄鳝精不过鳖”,既是对甲鱼灵性的赞美,也是对老憨技艺的肯定。他依靠对甲鱼习性的深刻理解,以传统方式(扣盆、鱼叉)捕捉甲鱼,与自然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获取资源却不破坏生态。这种技艺本质上是乡土智慧的体现,是人与自然的共生之道。
然而,当现代化浪潮席卷乡村,传统技艺的生存空间被挤压。水塘干涸、农药污染、“鳖扫光”毒药泛滥,老憨被迫远走他乡学习工业化养鳖技术。作者在此揭示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老憨从“捉鳖大王”变为“养鳖大王”,表面上是技术的进步,实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养鳖场中“饲料一喂,鳖仔像吹气球般膨胀”的描写,暗示了工业化生产对自然规律的粗暴干预。老憨的“成功”以牺牲甲鱼的天然属性为代价,最终也反噬到人类自身——女儿因食用激素甲鱼而早熟,成为科技失控的牺牲品。
这一转变隐喻了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悖论:人类试图通过技术征服自然,却因背离自然规律而陷入更深的困境。
二、甲鱼的象征:财富、贪婪与自然反噬
甲鱼在小说中是一个多层次的象征符号。首先,它是老憨赖以生存的资源,象征乡土社会中的自然馈赠。两只甲鱼换来媳妇的情节,既凸显了甲鱼的经济价值,也暗示了传统社会中物物交换的朴素伦理。其次,甲鱼成为老憨家庭幸福的载体:他通过甲鱼滋补妻子,使其从“病婆娘”变为“俏娘们”;女儿出生后,甲鱼更被视作“最佳营养品”。此时,甲鱼承载着老憨对家庭美满的期待,象征着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
然而,随着工业化养鳖的兴起,甲鱼的象征意义逐渐扭曲。饲料中的激素让甲鱼“速成”,其生物属性被异化为纯粹的商品。老憨对财富的追逐,使他忽视了甲鱼作为生命体的本质。最终,甲鱼从“养人之物”变为“害人之物”,女儿的身体异常成为自然对人类贪婪的审判。作者在此以残酷的笔触揭示了现代化陷阱:当自然被简化为牟利工具时,其反噬必然降临。
值得注意的是,老憨在悲剧后的怒吼“王八蛋啊”,既是对无良饲料商的控诉,也是对自身盲目追逐现代化的悔恨。甲鱼的“殇”,不仅是物种的消亡,更是人性与伦理的沦丧。
三、人物悲剧:乡土社会的失序与精神荒芜
老憨的形象极具代表性。他是传统乡土社会的“能人”,凭借技艺赢得尊重;但他也是现代化洪流中的“迷失者”,在财富诱惑下抛弃了与自然的契约。他的悲剧源于双重身份的撕裂:作为捉鳖人,他本应守护自然;作为养鳖商,他却成为生态破坏的共谋。这种矛盾在女儿患病时达到顶点——他试图用甲鱼滋养后代,却亲手将女儿推向深渊。老憨的嚎哭,是乡土社会在现代化冲击下发出的集体悲鸣。
妻子和女儿的命运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主题。妻子因甲鱼重获健康,又因甲鱼失去女儿的正常成长,这一循环暗示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与背叛。女儿的身体异化(早熟、发育异常)则成为现代化畸形的具象化呈现:在“速成”文化中,连生命都无法逃脱被催熟的命运。
此外,乡村的衰败背景为人物悲剧提供了土壤。田地被弃、水塘干涸、农药泛滥,这些细节勾勒出一个生态崩溃的乡土图景。当村民用“鳖扫光”毒杀甲鱼时,不仅毁灭了物种,也摧毁了延续千年的乡土伦理——敬畏自然、取之有度。老憨的悲剧,正是整个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序的缩影。
四、叙事策略:乡土寓言与现实主义批判
朱道能的叙事手法兼具寓言性与现实感。小说以甲鱼为线索,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象征体系:捉鳖代表传统,养鳖象征现代,女儿的疾病则是未来的警示。这种寓言结构使作品超越了具体事件的局限,具有普世意义。
同时,作者以现实主义笔法刻画细节,增强了文本的批判力度。例如,老憨用十年老鳖为妻子进补的情节,既符合民间“以形补形”的养生观念,又为后续的悲剧埋下伏笔;医生揭示激素危害时,老憨的迷茫与愤怒,精准呈现了底层民众在科技霸权下的无知与无助。这些细节使寓言骨架血肉丰满,让读者在具体可感的故事中反思宏观命题。
语言风格上,作者善用乡土俚语和比喻,如“媳妇模样天天变,可肚皮却一直没有变”“胖乎乎的,藕节似的”,既生动勾勒人物形象,又保留了浓郁的乡土气息。而“鳖扫光”“饲料一喂,鳖仔像吹气球”等表述,则以戏谑口吻讽刺了现代化的荒诞性。
五、伦理追问:科技发展与人性底线
《鳖殇》的核心矛盾指向科技伦理问题。养鳖场的技术神话建立在激素和速成饲料之上,这种“进步”以破坏生命自然规律为代价。老憨的困惑——“俺给孩子吃的是鳖,又不是饲料”——尖锐揭示了现代社会的认知断裂:人们只见产品的表象,却无视生产链中的隐性危机。
医生的质问“你们养甲鱼,难道不知道饲料含有啥成分?”更是直指资本与科技的合谋。在利润驱动下,生产者隐瞒真相,消费者盲目信任,最终导致悲剧。作者借此批判了现代社会对“效率”和“增长”的狂热崇拜,以及在此过程中人性底线的溃退。
值得注意的是,老憨的觉醒仅限于个体层面的痛苦,未能上升为对系统的反思。这种局限性恰恰反映了现实困境:个体在庞大的科技与资本机器面前,往往无力反抗,只能吞下苦果。
结语:在殇痛中寻找救赎之路
《鳖殇》的结尾充满绝望:老憨怒吼“滚!”,既是拒绝甲鱼交易,也是对现代化陷阱的无意识反抗。然而,这种反抗并未指向真正的出路。女儿的悲剧已成定局,乡村的生态伤痕难以愈合,甲鱼的“殇”成为时代之殇的隐喻。
朱道能通过这篇小说,发出了沉重的警示:当人类以征服者的姿态对待自然时,必将遭到自然的报复;当科技发展脱离伦理约束时,所谓的进步不过是加速毁灭的陷阱。老憨一家的命运,呼唤着对传统智慧的回归、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以及对科技伦理的严肃审视。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鳖殇”成为人类共同的殇痛。